那些年,平潭人的“做年”记忆
2025-02-07 10:06:18 来源:平潭网 作者:郑也 文/摄 部分图片为采访对象供图或资料图 漫画为赵曙合绘春节的热闹喧嚣渐渐散去,平潭的年俗文化依旧韵味悠长。近日,记者邀请李遵云、詹立新、念家圣、赖民四位平潭民俗文化专家,聆听他们口中交织着厚重历史与温情生活的年俗故事,探寻平潭那独具风情的年味记忆。

平潭文史专家 李遵云:
过平潭独有的特色文化年
平潭岛的过年习俗与记忆,在新年的鞭炮声与咸涩的海风中缓缓铺陈开来。北纬25°30′的阳光,轻柔地洒落在花岗岩垒砌的古厝上。斑驳的古灰墙上,一副用牡蛎灰调墨书写的白头春联,在海风的吹拂下微微颤动,悄然打开了李遵云的话匣子……
“相传明嘉靖四十年(1561年),倭寇烧杀掠抢,给平潭人带来伤痛。彼时除夕,为了纪念逝去的亲人,人们以白纸联、绿纸联代替红纸联贴在自家大门上。这份沉痛的记忆,逐渐沉淀、淬炼,形成旧时平潭人家贴‘白头联’的习俗,也成了平潭独特的过年风俗和文化韧性。”李遵云娓娓道来,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年俗密码,逐一鲜活起来。
在平潭方言里,藏着许多与年俗相关的俚语和童谣,它们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,例如,“初七人生日、初八上彩坪”等。其中,“初七人生日”,寓意着初七这天每个人都要过“人生日”,吃线面。李遵云告诉记者,旧时,在正月初七这天,人们除了吃长寿面外,还要吃两个煮鸡蛋,以此期盼新的一年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。
在李遵云的记忆里,平潭人过年后还要“做节”,俗称“过年过节”,即便是岛上最穷的人家,年节也要过,这种习俗要持续一整个正月。
过年期间,平潭人会集中举办婚礼,这也是平潭由来已久的传统习俗。“这与平潭的渔耕文化、特殊气候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:冬季海上风浪较大无法出航,因此渔民们有更充足的时间筹备婚礼;同时,过年期间亲朋好友们欢聚一堂,可谓天时地利人和,所以喜事大多集中在过年前后举行。”李遵云说,平潭还有一个‘闹元宵’习俗,在正月十五之前的一年内结婚的喜家,都要在元宵节晚上张灯结彩,摆上糖果、桂圆、饼干等甜品,新娘像结婚时一样梳妆打扮,端坐在新房,亲戚朋友则提着灯笼,成群结队到喜家家里‘闹元宵’‘闹新房’‘闹新娘’‘看新娘分喜糖’,旧时也称‘分甜’,意味着分享喜家的甜蜜。”
同样具有仪式感的还有拗九节。李遵云介绍,按传统习俗,每年正月二十九这天,凡是年龄中逢9的岁数(俗称“正九”)和年龄中逢9的倍数如18岁、27岁等(俗称“暗九”)的人,都要起早到别人家里去“过九”,祈盼能顺利过坎,时来运转。“这一民间传统‘过九’习俗,巧妙将周易数理与海洋信仰相互融合,让每一个与‘九’相关的年龄,都化作跨越风浪的航标。”李遵云说。
然而,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,年轻人的过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,许多传统文化中的年俗和习俗逐渐被简化、淡化甚至被遗忘。在李遵云看来,现在的年轻人在追求仪式感时,往往忽视了平潭年俗年味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与价值。“希望年轻人能重视并传承平潭海岛独有的年俗文化,不要让这些珍贵的独特的年俗在时代的浪潮中悄然消逝。”李遵云说。

平潭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詹立新:
在年味中延续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
新春佳节,詹立新的思绪被拉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那是一段充满烟火气与温情的岁月,也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年味记忆。
詹立新回忆,平潭筹备过年从“筅堂”开启,这是家家户户大扫除的日子。由于当时没有自来水,全家老小齐上阵,将家具搬到小溪、渠道或水井旁清洗,水岸边一片热闹繁忙,过年的序幕也就此拉开。
紧接着就是写春联,这是家庭文化传承的重要时刻。父亲书写春联时,詹立新和孩子们在一旁帮忙折纸、磨墨、张贴。父亲凝重的眼神和铁画银钩的楷体字,传递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。“那时没有印刷春联,每一副都是原创,写好的春联贴满家中木门,有时还会应亲邻之邀代写。”詹立新说,他热衷于到各家门口欣赏春联,从内容到字体细细品味,不经意间,这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国学教育方式。

除夕当天,全家人忙着准备美食,鱼粉、肉粉、炒米粉及炸鱼、炸虾等各类“炸料”必不可少,还要“做包”、蒸发糕,这些平日难得一见的美食,组成了当时的“满汉全席”。饭桌上,父亲那句“年年难过年年过”,既是家教,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安慰与庆幸。
除夕夜,父母会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,崭新的一角或两角纸币,虽不多,却是孩子们珍贵的“年终分红”。正月里,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去“岚城影院”看电影,《闪闪红星》《地道战》等革命英雄片深受欢迎。影院购票窗口狭小,买票如同抢票大战,抢到票的喜悦难以言表。影院门口还有人摆摊卖小人书,花花绿绿的小人书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,还成为他们接触美术、书法、文学的启蒙读物。
过年时,个人打扮也不能少。年前剃头,大年初一穿上崭新的、没有补丁的衣服,便是最好的装扮。“那时的穿衣准则是‘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’,与如今的时尚观念大相径庭。”詹立新笑着说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南街是平潭城关的经济文化中心,过年时充满极具诱惑力的气球、糖果、鞭炮,是孩子们心驰神往的所在。南街尾的文化站游园活动,尤其是有奖猜谜,让过年氛围达到高潮。彼时,平潭最高的建筑是中医院内的四层楼,在当时被视作“摩天大厦”,孩子们常爬到楼顶俯瞰,感受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。

半个世纪转瞬即逝,当年的生活虽然艰苦,但年味十足,那些酸甜苦辣的回忆构成了詹立新独特的青春印记。他无比怀念那段时光,既是对童年和青春的追忆,也是对那个时代精神的纪念。“在如今物资丰富的时代,延续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,或许是对传统年味最好的传承。”詹立新说。

实验区文化遗产专家库成员 赖民:
新春里的诗意“诗钟”
回忆起古早的春节,赖民感慨万千。每当新春来临,扫尘、祈年、置酒、焚帛等传统习俗必不可少,老少亲友相互拜年,其乐融融。迎灯之时,更是热闹非凡,台阁上词明戏、闽剧等精彩上演,盘诗对唱、丝弦十番,彻夜未息。木偶“闯神”,蛇灯舞动,金鼓齐鸣,震耀耳目。
在这浓浓的年味中,赖民认为“诗钟”文化独树一帜。1983年7月1日,赖民作为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,加入岚涛诗社,师从陈书坊、翁作春、吴金春等岚邑雅士,在多个春节与他们一起参加“诗钟”迎春活动。所谓“诗钟”,又称“截句”“折枝诗”,指在规定时间内,计时拈题,创作对偶句式的文学活动,既像文学游戏,又似文学竞赛。
早期“诗钟”以焚香计时,后来改用时钟。创作者需按照题目规定嵌字,依照七言律诗颈联、颔联的平仄要求撰成对子,充分展现艺术功力。例如,翁作春的《知言,七一唱》:“知和可贵宜循矩,言战无谋枉读兵”,巧妙地将“知”“言”二字嵌入句首,对仗工整,寓意深刻。
岚涛诗社的“诗钟”迎春活动别具一格,不用焚香,以座钟计时,评委当场亮分,评选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及优秀奖等,并当场颁奖。诗人们用平潭方言唱和,吟声琅琅,气氛喜庆热烈,参与者常常沉浸其中,欢声笑语不断。
平潭新春“诗钟”文化历史悠久。清朝时,平潭就涌现出蔚文诗社、西院诗会、兴文吟社、东岚吟社等文学社,彼时平潭诗人多达30余人。每到岁时节令,尤其是新春之际,诗人们焚香吟诵,尽享文学之乐。
如今,平潭文化昌盛,文学繁荣,一代文学才俊崭露头角。然而,赖民惋惜于“诗钟”这一传统文化逐渐式微。“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,能再次听到‘诗钟’在平潭大地上‘奏响’,让这一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”赖民期待道。

平潭作协副主席 念家圣:
笔墨、篮球赛里的年味传承
除夕夜,平潭东澳渔港,64岁的念家圣手握兼毫,在裁好的红纸上悬腕运笔。“这‘海上千帆归’的下联,得配‘门前万福来’才够气派。”墨迹未干的春联在咸涩海风中轻摆,将念家圣的思绪拽回1975年的除夕。那时刚满15岁的他,正为邻居亲友写春联。
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,手写春联不仅是对节日的装点,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。除了满足邻居亲友的需求,渔船、祖屋和单位的对联也出自他手。随着时代发展,春联内容更接地气,充满生活气息。念家圣考上大学后,还组织了写春联活动,吸引更多伙伴参与。
篮球赛也是平潭东澳春节的传统活动。念家圣热爱打篮球,他介绍,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东澳的春节篮球赛热闹非凡。当地国营单位众多,机关、学校和村队等十几支队伍参与其中,比赛持续数日。“这场比赛有效抵制了赌博打麻将、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,将民众引向积极团结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。”念家圣说。
此外,在那个科技尚不发达、文化生活相对单一的年代,看戏是春节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。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四郎探母》《铡美案》等经典剧目,让戏班子成为春节的“宠儿”。念家圣认为,看戏具有独特魅力:舞台上善恶分明,让观众爱憎分明;看戏时邻里相聚,寒暄问候,增进彼此感情;戏中人生百态,让观众在怀旧中得到情感释放。此外,还可借助看戏的时机进行宣传,使宣传深入人心。
除夕挂灯笼,正月十五“游上元”的游灯习俗,同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念家圣的父亲是带领游灯的重要人物。在乡下,一个自然村的几十上百户人家为一“境”,游灯时需经过每一户门前,这不仅是传统习俗,更是团结友爱的象征。
“尽管时代变迁,这些春节活动依然延续,只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。它们不仅保留了春节的喜庆氛围,更包含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。”念家圣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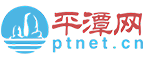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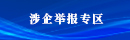
最热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