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潭特色小吃做出幸福年味
2025-02-07 09:38:40 来源:平潭网 作者:王焰 文/摄
特色小吃合集(从左至右依次为可可酥、拗九丸、薯渣饼)
每逢过年,最让平潭人想念的,莫过于小时候那熟悉而浓郁的“地瓜味”小吃。在游记民宿的厨房里,林大妹和杨天会正亲手制作着平潭特色的年味小吃:金黄酥脆的可可酥、Q弹柔韧的拗九丸和焦香软糯的薯渣饼。这些“地瓜味”小吃,曾是平潭人年节里重要的美食。从贫瘠年代的充饥口粮,到今日年味和年俗的象征,它们不仅承载着岚岛居民的生活记忆,也映照着平潭人的坚韧和智慧。
“过年嘛,就想自己做点老味道,炸点可可酥,包点拗九丸,再煎点薯渣饼,这样才有年味。”游记民宿主理人素白(化名)笑道,“我很喜欢吃这些东西,等会再给厨房布置一些红色的喜庆装扮,过年的氛围就更加浓烈了。年到了,我们要奔向新的希望。”

林大妹(左)和杨天会在和面
可可酥 年节最香的“嘎嘣脆”
薯片人人都吃过,但地瓜味的“平潭牌薯片”呢?地瓜粉做成的面团切成菱形状的小片下油锅一炸,膨胀变松,一口咬下去,油香四溢,这可是平潭小孩最喜爱的零嘴。
可可酥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,但每一步都要精准拿捏。“地瓜粉得与适量的热水混合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揉面时加入热水的比例很重要,热水多了,面团过熟,炸出来就会发硬;热水少了,面团太生,炸出来就不够酥。”林大妹一边揉面团,一边介绍。
面团静置片刻后,擀成一张巨大的薄片,再切成小小的菱形,这就是可可酥的原型。林大妹的刀工了得,三两下就切出了一堆整齐的面片。
“下锅咯!”她熟练地将一把面片抖散,倒入滚烫的油锅。
“滋啦——”热油瞬间将面片包裹,它们在锅里翻滚着,迅速膨胀鼓起,变得金黄酥脆。“一定要提前关火,用余热把它炸熟,就不容易糊。”林大妹用长筷快速翻拌,待颜色达到理想的金黄色,迅速捞起沥油。空气中弥漫着地瓜的甜香,令人垂涎。
一块刚出锅的可可酥,沾着滚滚的热气,油光在光线下微微泛亮。轻轻一掰,就能听到清脆的“咔嚓”声,焦脆的外皮应声断裂。入口瞬间,满满的油香在唇齿间炸开,带着红薯独有的甘甜,在舌尖化开。咀嚼间,那层层叠叠的脆感令人无比满足,香气顺着热度直冲鼻腔,唇齿间仿佛还留着刚出锅时的温度。吃完一片,手指上还沾着淡淡的油香,令人忍不住再伸手拿起下一块。
“小时候,每到过年,家家户户都会炸上一大盘,放在竹篮里,盖上一块红布。大人忙着干活,小孩子馋得不行,就偷偷掀开布抓上一把,‘嘎嘣嘎嘣’地吃。”林大妹笑着回忆。

捏拗九丸
拗九丸 地瓜粉包裹的甜蜜年味
“拗九丸名字虽然拗口,却是我们平潭拗九节,也就是正月最后一个逢九的日子必吃的美食。”素白介绍,拗九丸类似于缩小版的平潭“烧卖”,只是地瓜粉做的皮里面包的不是肉,而是用白糖、花生碎、芝麻等制作的甜馅。
据平潭县志记载,拗九节又叫“孝父节”,是平潭“八节”中最具有平潭特色的节日,无论有无“过九”,平潭人在拗九节这天都要包拗九丸,捏成烧卖或饺子的形状,或蒸或煮。吃了拗九丸,过完拗九节,平潭人才正式宣告“过年结束”。
厨房另一侧,杨天会正忙着做拗九丸。拗九丸的皮也是用地瓜粉和水调制而成的,取一小块面团,两只大拇指向内用力,借助食指和拇指的间隙旋转均匀用力,一个圆窝状的拗九皮就浮现于掌间了。杨天会熟练地舀起一勺甜馅,放在小碗状的面皮中央,再轻轻捏拢四角,就像一朵盛开的花苞。
下水烹煮片刻,再掀开锅盖,白雾瞬间升腾,拗九丸的香甜味弥漫开来。刚煮好的拗九丸,外皮晶莹剔透,柔韧Q弹。轻轻一咬,甜馅流出,花生和芝麻的香气瞬间在口腔中炸开,让人心生甜蜜。“小时候最喜欢抢刚出锅的拗九丸,一口咬下去,甜滋滋的,一整天都是好心情。”杨天会笑着说。

林大妹在磨薯渣
薯渣饼 记忆中的地瓜香
在所有“地瓜味”小吃里,薯渣饼大概是最质朴的一种。相比可可酥和拗九丸,它的身影如今已很难见到,甚至不少平潭年轻人都不曾了解过这道小吃。它不像可可酥那样金黄酥脆,也没有拗九丸的甜糯内馅,但正是这种未经雕琢的模样,在土生土长的平潭人素白的记忆里,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“小时候,粮食特别珍贵,过滤完地瓜粉后剩下的薯渣也不能浪费,大人们就用这个加点粉加点糖,煎成小饼子。”素白出神地看着阿姨翻动锅里的薯渣饼,悠悠地说,“薯渣饼口味独特又顶饿,虽然常被笑称是‘穷人饭’,却香得很。”
刚出锅的薯渣饼,带着热腾腾的烟火气,表面焦黄中透着一丝深褐,轻轻一按,能感受到饼身的韧劲。趁热咬下一口,首先涌上来的,是柔糯的内在,紧接着的是地瓜渣在锅中慢煎后的焦香,厚实的内里缓缓释放出地瓜本真的醇厚甜味。它不像精细研磨后的地瓜粉那样细腻,而是保留了地瓜最原始的纤维,咀嚼间,还能感受到一丝烟火气与土地的气息交织在一起。
这种独特的口感,让人一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物资不算丰富的年代。那时,家家户户都要靠种地瓜填饱肚子。红薯磨成粉,滤出的薯渣本是无用之物,但人们舍不得浪费,就想着法子将它利用起来。混入少许地瓜粉和水,摊成薄饼放在锅里慢煎,简单的食材,在铁锅的炙烤下,竟也成了一道饱腹又香气四溢的小吃。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精细的食物越来越多,薯渣饼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它曾经是老一辈人记忆中的“贫穷味道”,现在却成了一种罕见的传统风味,只有在一些老人家里,或者像林大妹和杨天会这样的老手艺人手中,才能再现这道带着时代印记的小吃。
素白回忆,小时候家里做薯渣饼,她总是站在灶台边,看着母亲用木铲慢慢翻动锅里的饼,那股煎烤出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,让人忍不住咽口水。等到饼子煎得焦香,母亲会掰下一小块递给她,虽然烫得她直吸气,她却舍不得放下,急急地吹凉后塞进嘴里,那种粗粝又甘甜的口感,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,成为故乡味道的一部分。
“现在的年轻人吃惯了细腻精致的食物,可能很难接受薯渣饼的口感,但对我们来说,它不仅仅是一种小吃,更是一种对过去的回忆,是平潭人‘靠地瓜度日’的生活写照。”素白感慨道,“有时候,人们以为它已经被遗忘了,但当你真的尝上一口时就会发现,那种味道一直都在。”
薯渣饼的价值,并不只是作为食物存在,它承载着那段朴素而坚韧的岁月,那种在物资匮乏中依然懂得珍惜、创造美味的智慧,以及每一口咀嚼间,时间留下的余味。
记者手记
地瓜香气里的平潭年节
“平潭岛,地瓜多,大米少。”就像民谣里唱的那样,许多人对地瓜的印象,依旧停留在它是过去平潭人的主食上,将它打上了关于那段贫瘠年代的标签。事实上,地瓜对平潭来说,远不止是食物那么简单,它见证了这片海岛的变迁,也塑造了平潭人的性格,承载着他们的乡愁与情感。

磨薯渣
地瓜对于平潭人有多重要?游记民宿主理人素白(化名)是这样描述的:老一辈的平潭人一生都与地瓜为伴,种地瓜、吃地瓜,连开口说话都是“地瓜腔”,年味美食里也都有着地瓜的影子。

素白为民宿挂上新春灯笼
平潭作家阿灿在其文章《灿说海坛》中写道:“平潭人对番薯的依赖更甚于其他地方——看看1922年农产物表的亩产量,当年粳米、大小麦的亩产是3石,花生是4石,而番薯则是20石。同样一亩地,番薯是花生、粳米、大小麦的五六倍!‘平潭地尽沙渍,稻田稀少,民食皆赖是物’,这话一点不虚。”
于是,耐贫瘠、抗风耐旱的红薯,也就是平潭人口中的地瓜,成了那时岛上的主要口粮。据何乔远《〈番薯颂〉序》中记载,“其初入吾闽时,值吾闽饥,得是而人足一岁。其种也,不与五谷争地,凡瘠卤沙岗,皆可以长。”地瓜“沙砾之地皆可种”的特性,让过去的平潭岛“饥焉得充,多蔫而不伤。下至鸡犬皆食之”,同时也造就了那时家家户户依赖地瓜的局面。
在过去,地瓜不仅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平潭人生存的依靠。从地瓜饭、地瓜粥,到地瓜粉、地瓜干,甚至连榨粉后的薯渣也被充分利用,平潭人的饮食与地瓜密不可分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,平潭人的饮食结构早已不再依赖地瓜果腹,但地瓜没有从餐桌上消失,以另一种形式留了下来——成为一道道承载乡愁的小吃。地瓜的质朴转化为逢年过节里的仪式感,为团圆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平潭味道。曾经象征艰难岁月的食材,如今成为节庆时刻的美味,它的角色转变,既是一种生活水平提升的象征,也是一种文化的沉淀。年味,正是在这些代代相传的“地瓜味”小吃中,变得更加鲜活而深远。
如今,年味的定义或许已经发生变化,鞭炮声减少了,春联走向印刷化,连年夜饭也有了速冻半成品的快捷选择。但当一块可可酥在齿间碎裂,当拗九丸的甜香在舌尖融化,当薯渣饼的烟火气萦绕鼻尖,我们依然能从这份熟悉的地瓜香里,找到平潭年节最本真的味道。这些由地瓜衍生出的传统小吃,连接着过去与现在,也串联起海岛人的乡愁与记忆。它们不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,提醒着我们,无论身处何方,家的味道始终不会改变,年味也从未走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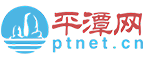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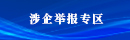
最热评论